晚飯時,外婆想喝口水,習慣性地喊了一聲:"映月……"
喊出口,她才反應過來,那個隨叫隨到的身影,已經不會再出現了。
客廳里,只有舅舅和舅媽觥籌交錯的喧鬧聲。
外婆的臉色變得無比難看,她看向江國棟:"國棟,扶我起來,喂我喝口水。"
舅舅正喝得興起,聞言不耐煩地擺擺手:"媽,你等會兒,我這正跟我朋友視頻呢,炫耀我的新車呢!"
外婆的臉瞬間沉了下去,她又看向舅媽劉芬。
劉芬正忙著拍照發朋友圈,配文是"感謝婆婆的厚愛,以後我們一定會好好孝順您的",她頭都沒抬:"媽,您渴了啊?那水壺就在您床頭柜上,您自己夠一下唄。"
自己夠一下?
一個癱瘓了二十年,脖子以下都動彈不得的人,怎麼自己夠?
外婆氣得嘴唇都在發抖,胸口劇烈地起伏著。
最終,還是我媽看不下去,走過去,默默地倒了水,用勺子一點一點地喂給她。
外婆喝著水,渾濁的眼睛卻死死地盯著那對沉浸在暴富喜悅中的兒媳,眼神里充滿了失望和憤怒。
我不知道她此刻有沒有後悔。
但這一切,都是她自己選的。
晚上,我給小姨送飯。
敲了半天門,她才打開一條縫。
看到是我,她空洞的眼神里有了一絲暖意,把我拉了進去。
房間裡,她的行李已經收拾好了,只有一個小小的行李箱。
裡面裝著幾件換洗的衣服,和幾本發黃的舊書。
"小姨,你真的要走嗎?"我把飯菜放在桌上,心疼地看著她。
她點點頭,臉上沒什麼表情:"清清,這個家,已經沒什麼值得我留戀的了。"
"可是你走了,能去哪兒呢?"我急切地問,"你身上有錢嗎?以後怎麼辦?"
她為了照顧外婆,二十年沒有工作,沒有社保,幾乎與社會脫節。
現在身無分文地離開,我不敢想像她要怎麼生活。
她沉默了片刻,然後從枕頭下拿出一個小小的布包,打開來,裡面是幾張零零散散的鈔票,加起來不過幾百塊。
"這是我以前存的一點零花錢,夠我撐一陣子了。"她笑了笑,笑容里滿是苦澀,"大不了,就去找份洗碗的工作,總不至於餓死。"
看著她故作堅強的樣子,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涌了上來。
我從包里拿出我的銀行卡,塞到她手裡:"小姨,這是我工作幾年攢的錢,雖然不多,但你先拿著應急。"
她卻像被燙到一樣,立刻把卡推了回來。
"不行,清清,這是你的錢,我不能要。"她的態度很堅決,"你以後還要結婚買房,用錢的地方多著呢。我不能拖累你。"
"什麼叫拖累!我們是一家人!"
"我很快就不是了。"她自嘲地笑了笑,然後從行李箱裡拿出一個陳舊的筆記本,遞給我,"清清,這個,你幫我收著。"
我接過來,發現那是一本手抄的詩集。
字跡娟秀,紙頁泛黃,上面寫滿了她年輕時的夢想和憧憬。
最後一頁,是一首沒有寫完的詩,日期停留在二十年前,外婆癱瘓的那一天。
"這些東西,帶著也是累贅,就當是留個念想吧。"她的聲音很輕。
我緊緊地攥著那本詩集,心如刀割。
我知道,她是真的要告別過去,告別那個被囚禁了二十年的自己。
第二天一大早,小姨就拉著行李箱,準備離開。
我和我媽去送她。
經過客廳時,外婆叫住了她。
"江映月,你真的要走?"外婆的聲音裡帶著一絲顫抖,不知道是氣的,還是怕的。
小姨停下腳步,卻沒有回頭。
"我昨天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你走了,誰來照顧我?"外婆的聲音拔高了,帶著一絲歇斯底里的質問。
這大概是她最關心的問題。
小姨聞言,終於回過頭,臉上帶著一抹冷漠的笑意:"誰拿了錢,誰照顧你。"
她說完,目光越過外婆,看向從房間裡探出頭來的舅舅和舅媽。
那兩人接觸到她的目光,立刻心虛地縮了回去。
"你……你這個白眼狼!我白養你了!"外婆氣急敗壞地咒罵起來,"你走了,你絕對會後悔的!離了這個家,你什麼都不是!你會餓死在外面!"
面對這些惡毒的詛咒,小姨只是平靜地看著她,眼神里沒有憤怒,只有一種深可見骨的悲哀。
"是嗎?"她淡淡地反問,"或許吧。但就算餓死,也比留在這裡,被你們吸干最後一滴血要好。"
說完,她拉著行李箱,毅然決然地走出了這個禁錮了她二十年的牢籠。
陽光灑在她消瘦的背影上,竟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壯。
我媽追了出去,塞給她一筆錢,她推拒了很久,最後只收下了兩千塊,然後上了一輛計程車,消失在車流中。
小姨走了。
這個家的平衡,徹底被打破了。
一場真正的風暴,才剛剛開始。
沒有了小姨這個免費保姆,照顧外婆的重擔,理所當然地落到了舅舅和舅媽的頭上。
然而,他們過慣了被人伺候的日子,哪裡會照顧人?
第一天,外婆想上廁所,舅舅江國棟笨手笨腳地抱她,結果差點把她摔在地上。
第二天,舅媽劉芬做飯,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外婆吃得直皺眉,還被她搶白了一句:"有的吃就不錯了,還挑三揀四!"
第三天,外婆半夜發燒,喊了半天,都沒人理。
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們才發現外婆燒得快說胡話了,這才手忙腳亂地把人送到醫院。
醫生檢查後,嚴厲地斥責他們:"病人是癱瘓病人,需要24小時精心護理!你們家屬是怎麼搞的?再晚來一會兒,人就危險了!"
舅舅和舅媽被訓得灰頭土臉。
從醫院回來後,兩人大吵了一架。
"都怪你媽!事兒真多!癱了還不安生!"
"你胡說什麼!那也是你媽!你當初拿錢的時候怎麼不說事兒多?"
"我拿錢是應該的!我是她兒子!可沒說拿了錢就得當牛做馬伺候她!"
他們的爭吵聲,毫不避諱地傳到了外婆的耳朵里。
躺在床上的老人,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了驚恐和悔恨。
她大概終於意識到,自己用1800萬,給自己換來的是怎樣兩個"孝子賢孫"。
04
舅舅和舅媽的"孝心"連一個星期都沒能維持住。
伺候癱瘓病人,是一件極其消磨耐心和體力的苦差事。
吃喝拉撒,按摩翻身,哪一樣都輕鬆不了。
以前有小姨在,他們從不覺得這是什麼難事。
可當這一切都落在自己頭上時,他們才體會到其中的艱辛。
僅僅幾天,舅舅江國棟就腰酸背痛,怨聲載道。
舅媽劉芬更是叫苦不迭,她那雙剛做了精緻美甲的手,現在卻要處理屎尿污穢,這對她來說簡直是酷刑。
於是,他們想到了一個"好主意"——請護工。
"媽,我們給您請個專業的護工吧,人家會照顧人,肯定比我們做得好。"舅舅一副"我為您著想"的嘴臉。
外婆躺在床上,冷冷地看著他:"請護工?那得花多少錢?"
"嗨,能花多少錢,"舅媽劉芬立刻接口,語氣輕飄飄的,"一個月也就萬兒八千的,咱們家現在有的是錢,這點小錢算什麼。"
"萬兒八千?"外婆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你們瘋了!一個月一萬,一年就是十二萬!你們這是想燒錢嗎?"
她節省了一輩子,對錢看得比命還重。
讓她一個月花一萬塊請人照顧自己,簡直是要她的命。
"那能怎麼辦?"舅舅的耐心也耗盡了,"我們倆都得上班,總不能為了照顧你,把工作都辭了吧?再說了,我們也不會照顧啊,萬一再把你弄進醫院怎麼辦?"
"以前映月是怎麼照顧的?她一個人不也照顧得好好的?"外婆下意識地就拿小姨做對比。
這句話,徹底點燃了舅媽劉芬的火藥桶。
"媽!您還好意思提江映月?"她尖聲叫了起來,"您要是覺得她好,您把她叫回來啊!哦,不對,是您自己把她氣走的!錢您一分不給人家,現在還想讓人家回來當牛做馬?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
"你……"外婆被她堵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氣得渾身發抖。
"行了!都少說兩句!"舅舅不耐煩地打斷了她們,"請護工的事就這麼定了!錢我來出!"
他表現得財大氣粗,仿佛那1800萬是他自己掙來的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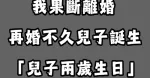
 武巧輝 • 5K次觀看
武巧輝 • 5K次觀看
 楓葉飛 • 3K次觀看
楓葉飛 • 3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