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個星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卻形同陌路。
她依然會做好飯,洗好衣服,把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
而我,則用沉默和無視來表達我的抗議。
我們之間沒有任何交流,連眼神的碰撞都吝嗇給予。
家裡的空氣,壓抑得仿佛能擰出水來。
我以為我的強硬態度,會讓她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會讓她主動來向我坦白,解釋一切。
然而,我錯了。
林晚比我想像的要固執得多。
她什麼也沒說,只是默默地承受著我的冷暴力,那雙曾經明亮愛笑的眼睛,也一天比一天黯淡下去。
周末,我媽打來電話,語氣里透著一絲不易察奇的興奮和炫耀。
"兒子,晚上帶小晚回家吃飯。我讓你哥也過來,一家人好久沒聚了。"
我媽是個典型的農村婦女,好面子,愛攀比。
自我出人頭地後,她在村裡走路都帶風。
每次我回家,她都要拉著我,挨家挨戶地去炫耀她有個在城裡當大老闆的兒子。
對於林晚這個兒媳婦,她一開始是滿意的,漂亮、聽話。
但自從不知道從哪裡聽說了林晚總跟娘家說我"月薪五千"的閒話後,她對林晚的態度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處處看她不順眼。
我本想拒絕,但一想到能藉此機會,讓我媽敲打一下林晚,讓她知道這種謊言的危害,便鬼使神差地答應了。
"好,媽,我們晚上準時到。"
掛了電話,我走到正在陽台晾衣服的林晚身後,用毫無感情的語調通知她:"晚上回我媽家吃飯。"
她的背影僵了一下,然後慢慢轉過身,看著我,眼神裡帶著一絲懇求:"陳陽,我們……能不去嗎?"
"為什麼不去?"我冷笑,"怎麼,怕我媽當著我的面,揭穿你的謊言?林晚,你也有心虛的時候?"
她被我這句話刺得臉色發白,嘴唇顫抖著,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最終,她只是低下頭,輕聲說:"好,我去換衣服。"
看著她落寞的背影,我的心裡沒有絲毫快意,反而更加煩躁。
傍晚,我們開車回到我父母住的老小區。
一進門,就聞到滿屋的飯菜香。
我媽熱情地迎了上來,接過我手裡的水果,卻連個正眼都沒給林晚,只是陰陽怪氣地說:"喲,我們家的大忙人回來了。小晚啊,你可得好好照顧陳陽,他現在可是咱們家的頂樑柱,一個人要養活一大家子,可真是不容易啊。"
林晚的臉"唰"地一下白了,她侷促地站在門口,手裡提著的補品顯得格外尷尬。
我哥陳峰和我嫂子也從廚房裡走了出來。
陳峰比我大五歲,從小就好吃懶做,沒什麼大本事,在一家工廠當保安,收入微薄。
我嫂子更是個眼高手低的,整天琢磨著怎麼占便宜。
他們倆一唱一和,將我媽那套"哭窮"的理論學了個十足。
"就是啊,弟妹,"我嫂子皮笑肉不笑地看著林晚,"我們家陳陽現在出息了,你可得把錢看緊點。聽說你跟娘家說,他一個月才掙五千?哎呀,這可不行,太實在了。現在的親戚,那都是喂不熟的狼,你越是哭窮,人家越是覺得你好欺負,什麼事都想來占點便宜。"
這話明著是為我說話,實際上句句都在敲打林晚,暗諷她娘家就是那"喂不熟的狼"。
我媽立刻接上話茬,聲音拔高了八度:"可不是嘛!有些人家,嫁了女兒就跟賣了女兒一樣,恨不得把女婿家都給搬空!我們陳陽心善,不懂得拒絕,小晚你身為妻子,就得替他把好這個關!別什麼錢都往娘家劃拉,得先顧著我們陳家!"
一時間,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林晚。
她孤零零地站在那裡,臉色蒼白如紙,雙手緊緊地攥著衣角,像一個等待審判的犯人。
我坐在沙發上,冷眼旁觀。
我承認,這一刻,我心裡是有一絲扭曲的快意的。
我就是想讓她嘗嘗,被至親誤解和羞辱的滋味。
我就是要讓她明白,她的那個可笑的謊言,不僅傷害了我,也讓她自己在我的家人面前,變得如此不堪。
林晚深吸了一口氣,抬起頭,目光卻越過我媽和我嫂子,直直地看向我。
那眼神里,有失望,有悲傷,還有一絲我讀不懂的決絕。
她沒有為自己辯解一句,只是默默地走到餐桌旁,開始幫忙擺放碗筷,仿佛剛才那場針對她的批鬥會,根本不存在一樣。
她的沉默,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讓我媽和我嫂子都覺得有些無趣。
飯桌上,氣氛詭異。
我媽還在喋喋不休地炫耀我的成就,說我最近又簽了個大單,公司獎勵了多少錢。
而我哥陳峰,則在一旁不停地給我灌酒,眼神閃爍,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林晚全程低著頭,默默地吃飯,偶爾給我夾一筷子菜,動作輕柔,卻帶著一種疏離的客氣。
我能感覺到,她正在用這種方式,在我們之間築起一道高牆。
酒過三巡,陳峰終於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
他端著酒杯,搭著我的肩膀,大著舌頭說:"好弟弟,哥……有件事想求你。"
我媽立刻在一旁敲邊鼓:"陳陽啊,你哥準備買房了,看中了市中心的一個樓盤,就是……首付還差那麼一點。你現在出息了,可得幫幫你哥。咱們親兄弟,打斷骨頭還連著筋呢!"
我心裡"咯噔"一下,最擔心的事情,還是來了。
03

"差多少?"我放下筷子,心裡已經有了一股不祥的預感。
我媽和我哥對視了一眼,我嫂子搶著開口,聲音又尖又亮:"不多不多,也就三十萬!對你來說,不就是幾個月的工資嘛!陳陽,你可不能當白眼狼啊,你忘了你上大學的學費,還是你哥輟學打工給你湊的呢!"
又是這套說辭。
每次他們想從我這裡要錢,都會把這件陳年舊事搬出來,像一道免死金牌。
當年我哥確實為了我輟學,但他打工的錢,大半都拿去吃喝玩樂了,真正用在我身上的,不過寥寥數千。
但這筆恩情,在他們的嘴裡,卻被無限放大,成了一筆我永遠也還不清的債。
三十萬。
這個數字像一塊巨石,重重地壓在了我的心上。
這幾乎是我手頭所有的流動資金。
我下意識地看了一眼林晚。
她依然低著頭,仿佛沒聽到我們的話,只是專注地挑著碗里的魚刺,動作慢條斯理。
但她微微泛白的指節,還是暴露了她內心的不平靜。
我媽見我沉默,立刻不高興了,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
"怎麼,你不願意?陳陽,我可告訴你,你哥是你唯一的親哥!他現在有困難,你不幫誰幫?難道你還指望你那個只會哭窮,一毛不拔的老婆嗎?"
這話一出,空氣瞬間凝固。
我看到林晚挑魚刺的手,猛地頓住了。
她緩緩抬起頭,第一次正視我媽,眼神冰冷得像一塊寒冰。
"媽,陳陽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三十萬,不是個小數目。"
這是她今晚說的第一句話,聲音不大,卻清晰地傳到了每個人的耳朵里。
"喲,我當是誰呢,原來是我們的『五千塊』媳婦開口了。"我嫂子立刻陰陽怪氣地接話,"怎麼,怕我們占了你家的便宜?你放心,這錢算我們借的,以後肯定還!不像有些人,只會往娘家搬東西,那才叫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呢!"
"你!"林晚的臉瞬間漲得通紅,胸口劇烈地起伏著。
"我怎麼了?我說錯了嗎?"我嫂子得理不饒人,雙手叉腰,像一隻好鬥的公雞,"你自己跟你媽說陳陽一個月就掙五-千,現在我們借錢,你又說三十萬不是小數目。你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還是說,你早就知道陳陽不止掙五千,故意瞞著我們大家,把錢都攢著,準備貼補你娘家?"
這番誅心之論,實在是太過惡毒。
連我聽了,都覺得有些刺耳。
我媽也反應過來,一拍大腿,指著林晚的鼻子罵道:"好啊!林晚,我總算看明白了!你這個女人,心機太深了!你是不是早就把陳陽的工資卡捏在自己手裡了?你天天跟我們哭窮,就是為了防著我們,怕我們找陳陽要錢是不是?你安的什麼心啊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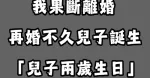
 武巧輝 • 5K次觀看
武巧輝 • 5K次觀看
 楓葉飛 • 3K次觀看
楓葉飛 • 3K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