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弄丟5歲妹妹,20年後參加同事婚宴,新娘一句話讓他徹底破防
同事婚禮上,林海不由自主的看向新娘。
看清新娘的面容後,林海明顯愣了一下,他覺得新娘的面容十分熟悉。
當林海看到新娘嘴角的那顆痣時,他徹底不淡定了。
他瘋了一樣衝上台抓住新娘的胳膊,在眾目睽睽之下他直接哭出了聲。
「小雅,我……我終於找到你了。」 說完他泣不成聲。
誰知新娘卻衝著他冷冷開口:「你是誰?」
這句話讓林海瞬間崩潰。
01
林海至今仍能清晰地回憶起那個下午的蟬鳴,聒噪得像是要把人的耳膜撕裂。
五歲的妹妹小雅穿著那件他最熟悉的鵝黃色小裙子,裙擺上繡著兩隻歪歪扭扭的黃色小鴨子,那是媽媽親手繡的。
她軟軟的小手信任地蜷在他的大手裡,因為剛吃完一根老爺爺賣的糖畫,指尖還黏黏的。
「哥哥,蝴蝶!」她忽然鬆開手,跌跌撞撞地追著一隻菜粉蝶跑進街心公園的人流里。
鵝黃色的身影在陽光下閃了一下,像一顆溫暖的小星星。
林海只是彎腰系了一下鬆開的鞋帶,最多十秒鐘。
當他再次抬起頭時,竟意外發現那片鵝黃色消失了。
鋪天蓋地的蟬鳴聲,瞬間變成了尖銳的耳鳴。
「小雅,小雅!」他驚慌的大喊,最後是撕心裂肺地哭嚎。
街心公園的綠蔭變得猙獰,每一個路過的人都像是藏起他妹妹的壞人。
那天下午,八歲的林海把自己的人生。
連同那個穿著鵝黃色裙子,笑起來眼睛彎彎像月牙的小女孩,一起弄丟了。
此後的二十年,那個十秒鐘的瞬間,成了林海生命中無法暫停,一直不停循環播放的痛苦的片|斷。
每一次回放,都伴隨著更深的悔恨與無力的窒息。
他們的家庭因此蒙上痛苦的陰霾,母親的眼睛總是紅腫的,父親則一夜白頭,家裡再也沒有聽到歡聲笑語。
林海背負著這座名為「愧疚」的大山,艱難地前行。
他大學選擇了刑偵專業,畢業後成了這座城市裡最出色的刑警之一。
他偏執地辦理每一樁兒童走失案,螢幕上的每一個失蹤兒童信息都讓他看到小雅的臉。
他辦公室里有一個加密的文件夾,裡面只有一張小雅笑得露出豁牙的照片,和一張根據年齡增長模擬繪製她二十歲模樣的畫像。
畫像上的女孩,眉眼間依稀有小時候的影子,嘴角有一顆小小的痣。
這是當年做模擬畫像的同事,根據林海「好像嘴角有個小點點」的模糊記憶加上去的,林海並不確定,但他把這顆痣當成了尋找到小雅的依據。
二十年了,他從未停止過尋找。
只是茫茫人海,希望如同風中殘燭,微弱得讓人不敢直視。
02
刑警隊的活兒沒有晝夜,又一樁大案告破。
連續熬了幾個大夜的林海被同事們強行推出來參加周末的婚宴。
「頭兒,你必須去,張珂好歹跟你同期進的局裡,你不能又不合群。」手下小陳直接把請柬塞進了他的警服口袋裡,讓他無法拒絕。
林海揉著發脹的太陽穴,最終還是答應了。
他換上一身熨平的藏藍色西裝,刮凈了胡茬,但眼底深藏的疲憊卻不是一套西裝能掩蓋的。
宴廳里張燈結彩,拱門處還擺放著新郎和新娘的婚紗照,到處洋溢著喜悅。
林海安靜地坐在同事一桌,看著舞台上西裝筆挺,笑容滿面的新郎張珂。
他心裡是為兄弟感到高興的,只是那份喧囂似乎隔著一層無形的屏障,無法真正抵達他的內心深處。
林海習慣性地摩挲著右手虎口處一道極淺的舊疤,那是小雅兩歲時咬的,因為他搶了她的玩具蘋果。
司儀熱情洋溢地請出新娘子,燈光聚焦,宴會廳的門緩緩打開,新娘挽著父親的手臂踏著花瓣走了過來。
她一襲聖潔的白紗,美麗不可方物,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光暈。
林海隨著眾人鼓掌,目光溫和地落在新娘臉上。
他突然有股莫名的熟悉感。
一種毫無由來的熟悉感,穿透了那層隔絕喧囂的屏障,直刺心臟。
他下意識地坐直了身體,刑警審視細節的本能瞬間壓倒了一切。
他的目光緊緊跟隨著新娘的臉,她的眉眼,還有笑起來的弧度簡直和小雅小時候一模一樣……
司儀正在活躍氣氛,說著俏皮話:「我們的新郎官張珂同志,是我們人民的守護神,破案眼光那叫一個毒辣,沒想到找媳婦兒的眼光,更毒辣,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們這麼美麗動人的柳薇薇做他的新娘。」
台下爆發出善意的笑聲。
林海卻笑不出來。
柳薇薇?
她不叫小雅。
是啊,她怎麼可能是小雅呢?
他心底剛燃起的一點火星,瞬間黯了下去。
他心想:我真是想小雅想瘋了,從那時起無論看誰都覺得像小雅。
婚禮流程一項項在有序進行著,到了新人敬酒的環節時,張珂帶著新娘一桌一桌地走來敬酒。
輪到同事這桌時,氣氛更加熱烈。
大家一邊起鬨一邊灌酒,很快張珂就顯然喝得有點多了。
他的臉紅撲撲的,用力拍著林海的肩膀向妻子介紹:「這是海哥,我們老大,也是局裡最牛的神探,薇薇,快,敬海哥一杯,以後有啥事,找海哥最好使。」
新娘柳薇薇端著酒杯,落落大方地微笑著看向林海。
燈光下,她的面容更加清晰。
林海的心臟又一次不受控制地劇烈跳動起來,那股熟悉感幾乎要讓他窒息。
他努力維持著鎮定,端起自己的酒杯。
「海哥,謝謝您來參加我們的婚禮,張珂經常提起您,說您特別照顧他。」新娘的聲音溫婉動聽,帶著一絲甜意。
她微微仰頭,準備飲下杯中酒。
就在那一瞬間,林海的瞳孔驟然收縮。
新娘舉杯的右手,虎口處有一道極淺極淺,形狀如月牙形的白色舊疤。
時間仿佛在瞬間凝固靜止,所有的喧囂潮水般褪去,世界只剩下那道疤。
林海的呼吸停了,血液在耳膜里轟隆作響。
那是……那是小雅兩歲時咬的疤,因為他搶了她的玩具蘋果。
位置、形狀、甚至那微微泛白的陳舊顏色都一模一樣。
他猛地抬起頭,目光像鷹一樣死死鎖住新娘的臉。
所有的冷靜自持,以及刑警的沉穩,在這一刻碎得乾乾淨淨。
他的異常太過明顯,整桌熱鬧的氣氛瞬間冷了下來,同事們疑惑地看著他。
新娘柳薇薇也被他過於銳利,甚至可以說是失禮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她重重放下了酒杯。
03
林海什麼也顧不上了。
他死死盯著她的嘴角,聲音因為極度緊張顫抖得不成樣子:「你……你嘴角的那顆痣請問是天生的嗎?」
他記得。
他記得那張模擬畫像,他當時和同事打賭了,就賭那顆他並不確定的痣。
柳薇薇被他突兀而奇怪的問題問得有些莫名其妙,下意識地抬手摸了摸自己右嘴角那顆幾乎看不見的小痣。
她的臉上掠過一絲驚訝和迷惑,顯然沒想到這位第一次見面的刑警大哥會問這樣一個關於她容貌細節的問題。
她搖了搖頭,似乎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好笑。
自然而然地用帶著一點本地人特有的,軟糯的尾音緩緩回答:「這不是痣啊,是小時候偷吃我爸剛熬好的花生糖不小心被燙了一下,最後留了個小點點,隨著年齡增長都快沒啦。」
「花生糖。」
「被燙的。」
「不是痣。」
每一個字,都像一記重錘狠狠砸在林海的心臟上。
那不是痣,是燙的疤痕。
林海記得二十年前的那個下午,他帶小雅去買糖畫。
她饞隔壁攤子熱騰騰的花生糖,拽著他的衣角哼哼唧唧,他沒給她買,只因怕燙著她。
如果……如果當時他給她買了……也許就沒有後面的事了。
巨大的無法言喻的情感像海嘯般席捲而來,瞬間衝垮了他二十年來用鋼鐵意志築起的所有堤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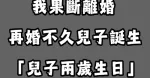
 武巧輝 • 2K次觀看
武巧輝 • 2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楓葉飛 • 2K次觀看




















